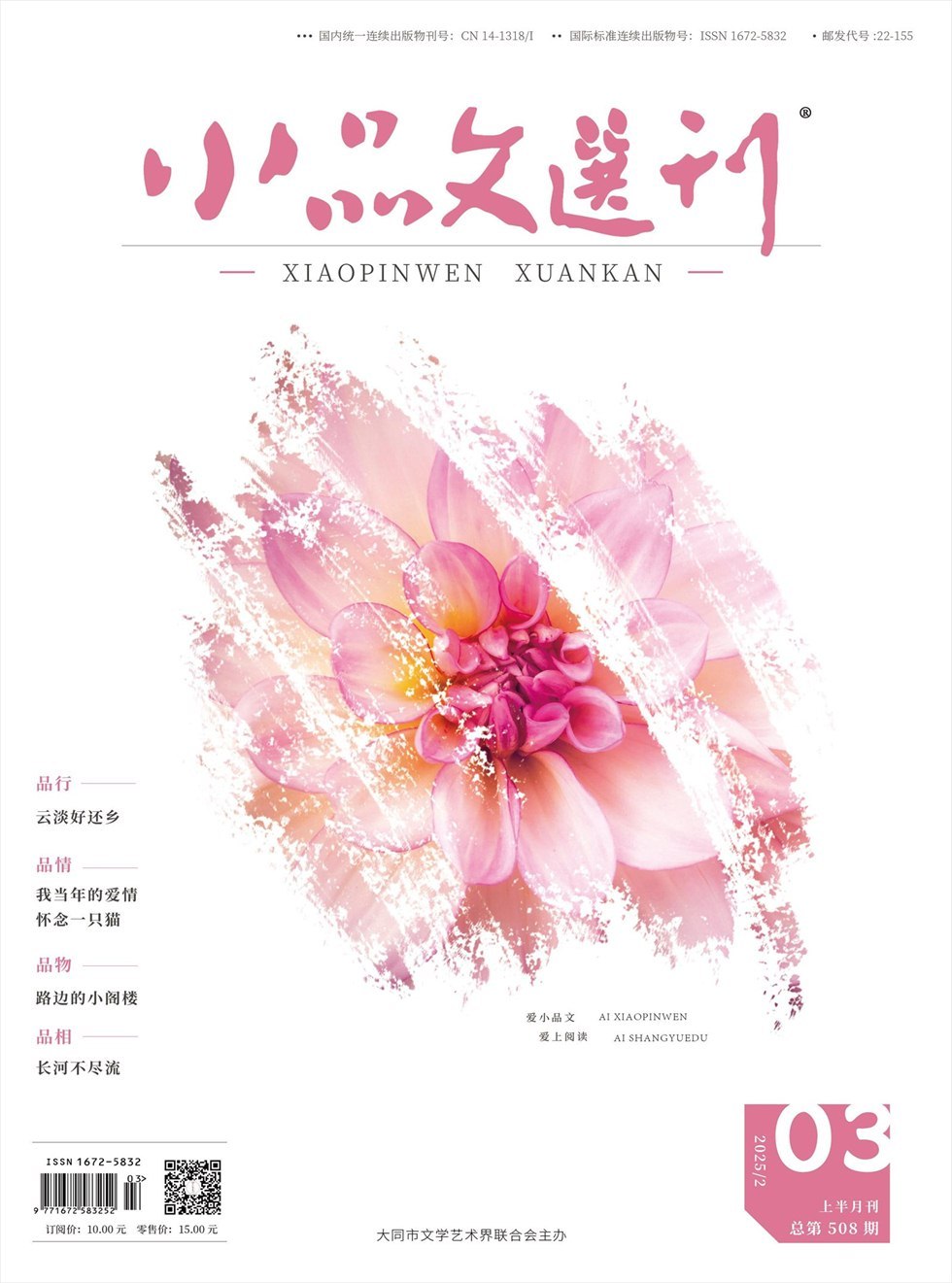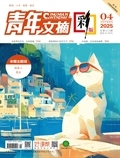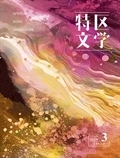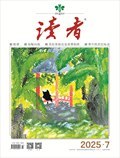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小品文选刊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书代替不了世界
卷首语 | 书代替不了世界
很多人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、头顶青天的伟人,事实上,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,弱得多。因此,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、更强烈。对他本人来说,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。艺术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痛苦,通过这个痛苦,他使自己得到解放,去忍受新的痛苦。 书代替不了世界。在生活中,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,都有他的任务,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。比如说,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
-
品行 | 云淡好还乡
品行 | 云淡好还乡
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,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。园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,蝴蝶无奈地蜕化和死亡,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它虫子弥留之际的尸衣。盛夏时节曾喧器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得如一个受孕的女人。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,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。 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,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。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,这霜就会消失,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
-
品行 | 回乡之路
品行 | 回乡之路
五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,我的后父不在了。得知消息后,我连夜驱车往沙湾县赶,那夜正刮着北风,漫天大雪,在昏暗的车灯中,从黑暗落向黑暗。那场雪仿佛是落给一个人的,因为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赶到沙湾县时,后父的遗体已被家人安置在殡仪馆,他老人家躺在新买来的红色老房(棺材)里,面容祥和,嘴角略带微笑,像是笑着离开的。 后来听母亲说,半下午的时候,我后父把自己的衣物全收拾起来,打了包。母亲问他,你
-
品行 | 一条古街的温柔
品行 | 一条古街的温柔
入口处,男女老少仍络绎不绝,有的进了沿途店铺,有的直奔舞台。高耸的门牌楼下,几个年轻人驻足,他们仰头看着灯火映照下的“瞻岳”二字,用手机认真地拍照,想要把每个细节都收入记忆。少顷,他们说说笑笑地朝古街纵深而来,步履轻盈,活力四射…… 那是秋季的一天。 在声嘶力竭的鸣笛声中,一列蒸汽机车犹似气喘吁吁的老牛,缓慢停靠在京汉铁路一等站——保定府站。很快,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下了火车。朝四周遥望片刻,
-
品行 | 云端上的小镇
品行 | 云端上的小镇
这是一座隐在云端上的小镇。 小镇不大。主街东西走向,长不过四五百米,数百住户。一户炒菜,家家都闻肉香;夫妻拌嘴,邻里都知原委。 小镇物产富饶。茶树在富硒土壤里生长,造就了其上佳品质。豆腐鲜嫩无比,很多人慕名而来品尝。黄桃、砂梨香气袭人,能将人的馋虫勾出来。 小镇很美,山水相依,云腾雾绕,如铺开的一张水墨画卷。 小镇很老,一座始建于唐朝时期的古寺密印寺,历经一千余年风雨洗礼,屹立在这一方山水
-
品行 | 桂湖漫步
品行 | 桂湖漫步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……”这是明代文学家杨慎(号升庵),在谪戍云南永昌(今保山)途中,写下的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。借景抒情,豪放中有含蓄,高亢中有深沉。 深秋时节,我前往新都桂湖,寻觅杨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蛋黄般的太阳穿透薄薄的雾霭,焐干潮湿的川西坝子,跟随我们一路朝南。游览完千年名刹宝光寺,已临近中午。吃过黄豆汤、嫩三鲜,便直奔桂湖公园。
-
品物 | 路边的小阁楼
品物 | 路边的小阁楼
自那年冬天开始,每次路过那里,我都忍不住深情地一瞥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——没有想到的还有,那一座小阁楼与历史悠久的105国道,因高速公路的出现,都离我渐行渐远,最终湮灭在岁月的烟雾里。 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,正是个贪玩的年龄。我大姑到她的小姑,也即是我的小姑奶奶家玩,不知怎么带上了我。小姑奶奶家依山傍水,门前有一条大沙河。对娘家侄女和侄孙子的到来,小姑奶奶一家显得非常热情。家里杀鸡蒸面,忙得不亦乐乎
-
品物 | 捡地软
品物 | 捡地软
在我的家乡“西海固”,有一种野生的菌类名叫地软。亦称地衣、地耳、地皮菜,黑色,状如铜钱,一串串、一片片,生来无根,栖身于荒山、草滩、田埂的地皮上。冬雪融化之际,农人在忙完一年的农事之后,暂得偷来片刻的闲适,此时,地软子经雪水的浸润舒展开了身子,只见年轻的媳妇子、娃娃伙们会趁着冬闲,挎着竹篮,端着脸盆,去荒坡野地上拾地软。据说它是一种天然的保健食品,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营养价值极高。用地软子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