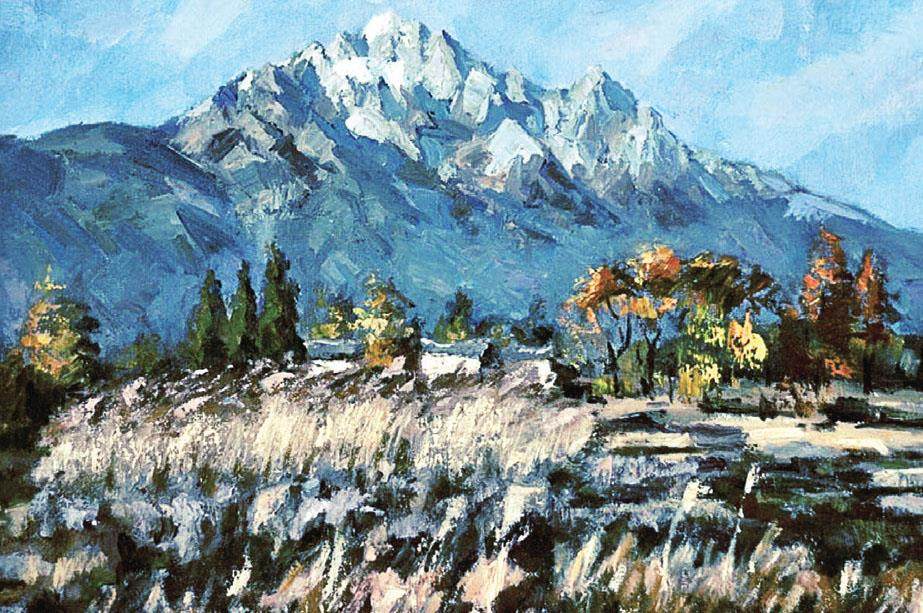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壹读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
名家有约 | 丽江木氏与鸡足山(外一篇)
名家有约 | 丽江木氏与鸡足山(外一篇)
-

实力青年 | 片多爷爷(组诗)
实力青年 | 片多爷爷(组诗)
-
小说空间 | 春风大雅
小说空间 | 春风大雅
一 罗万春像是被人抽走了骨架一般,有气无力地瘫坐在一堆干麻袋上。厂子里依旧车来车往,人出人进。喧嚣之声如同气浪一般向四面膨胀,突然一阵汽车喇叭声响起,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猛地扎在他的胸口上,让他孱弱的身子好似一个被戳破的轮胎,突地一下冲到了半空之中,待气流放尽,又重重地摔了下来。“嘭”地一声被砸得血光四溅,顿时感觉整个天地都变成了血红色。 我都快要死了! 罗万春在心里想。可偏偏有一个声音却让他不
-
散文天地 | 巴哈咏叹调
散文天地 | 巴哈咏叹调
1 最初,巴哈的唱腔是嘶吼的,是叫嚣的,是抓狂的。 我从没想过,进入这个满怀期待的名叫巴哈的古村落,要从一场骂架开始。 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骂架的人自然不是我。骂架的是住在鸳鸯湖边的两拨人。 那天下午,在一群又一群奔着鸳鸯湖碧绿的水、奔着鸳鸯湖情爱的噱头远道而来的游客的围观下,两拨人拉开架势,摆出阵仗,女人打头阵,男人殿后。双方把最肮脏最污秽最邪恶的词语都派上用场。很多词还被他们反复使用,
-
散文天地 | 大地的脉络
散文天地 | 大地的脉络
一 1967年冬,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,晨曦在浓如墨汁的黑夜中缓缓晕开,大地仍然一片晦暗。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,踏上了去异乡的路。泥路上结着薄冰,踩上去嘎吱作响,引来一阵有气无力的狗吠,寥寥几声后复归于平静。 天空呈一片均匀的铅灰色,远山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,裸露出满是伤痕的赭红色的胸膛,看不到一丝绿意。山冲一片寂静,苍茫的天地间,只有寒风的呼啸声和父亲的脚步声。寂静让饥饿的感觉来得稍微慢一些,却又
-
散文天地 | 植物的美意
散文天地 | 植物的美意
鸡嗉子 娘家院子里长着一棵鸡嗉子树,但鸡嗉子这个名称,我是从宣威作家叶浅韵老师的朋友圈知道的。去年一看到叶老师发的鸡嗉子果图片,就确定我娘家的那一棵之前不知道叫什么的树就是鸡嗉子了。 我父亲生前非常勤俭,常常在房前屋后给我们栽种别人家没有的果木,过去我们房前长着的砂梨树、杏树为村中独有,现在园子里的柿子树为当地独有,可以说,过去我家的很多果木是村中第一家栽有的。父亲在世时栽种在院子的果木,除了
-
诗歌方阵 | 隐匿的河源(组诗)
诗歌方阵 | 隐匿的河源(组诗)
迁徙的队伍登高向北 来到长江源区 与牦牛为伴,拓展生存之路 数年后,一对藏族情侣 翻山越岭寻找源头 隐匿的河源似乎在跟他们捉迷藏 无法预知的未来 或许曾在梦中有过暗示 当卓玛爱一个人的时候 脑海中不免掺杂幻想 将对方幻想成神的模样 幻想未来生活的细节 连他咳嗽的频率也能感知到 为了与扎西尼玛在一起 不停自我雕琢,用时间缝补内心 相信有一天能凿开挡在彼此之间的巨石 殊
-
诗歌方阵 | 日常随记(组诗)
诗歌方阵 | 日常随记(组诗)
立冬以后 蓝天输掉白云直到蔚蓝透明 江河输掉丰腴直到牙床裸露 树木输掉树叶直到伶仃孤苦 往后的每个阴郁的早上 都是对雪的期待 雪已经下在石佛山 下在万格山 山太高路太远 睫毛簌簌掉下 一日一日输走的一天一天 门扉的沉寂愈发轰隆 只有落叶杂草的脚步在徘徊 从窗口望去 从窗口望去是对面的红房子 普米族人家的屋顶飘着经幡 更远处是杂乱的建筑的屋顶 太阳能板和水桶的高地 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