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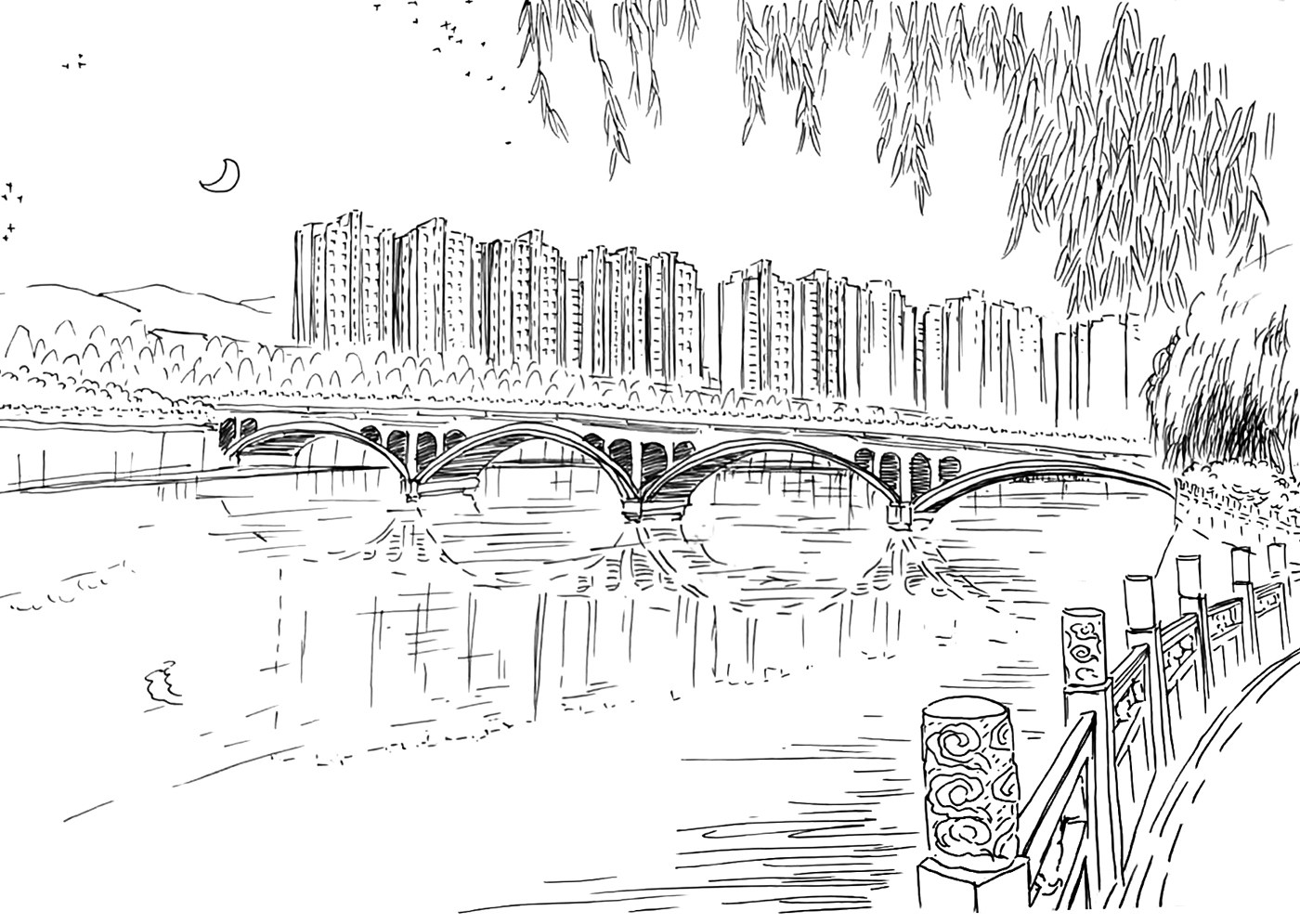
开篇作品 | 短篇小说三题
开篇作品 | 短篇小说三题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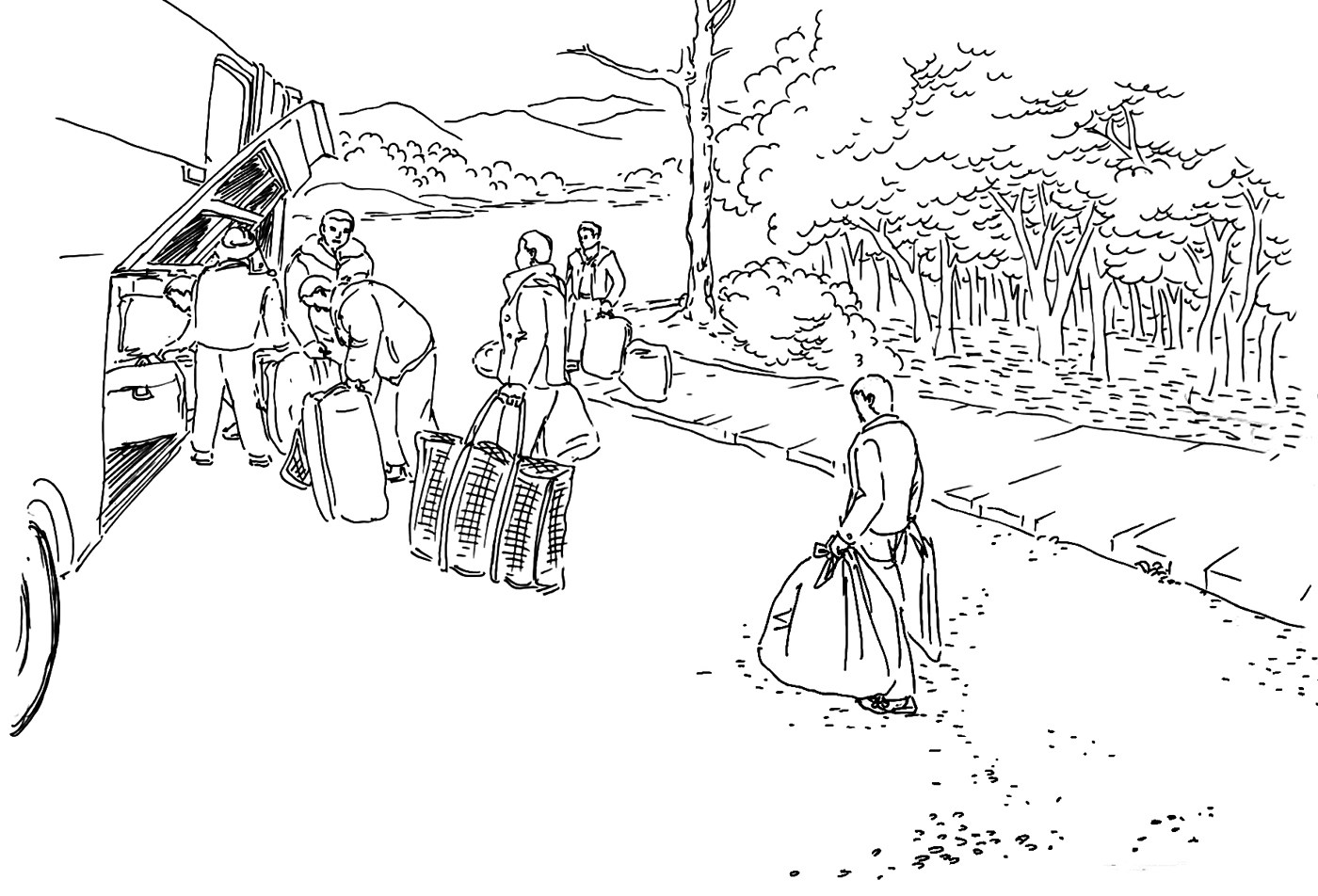
小说平台 | 后 土
小说平台 | 后 土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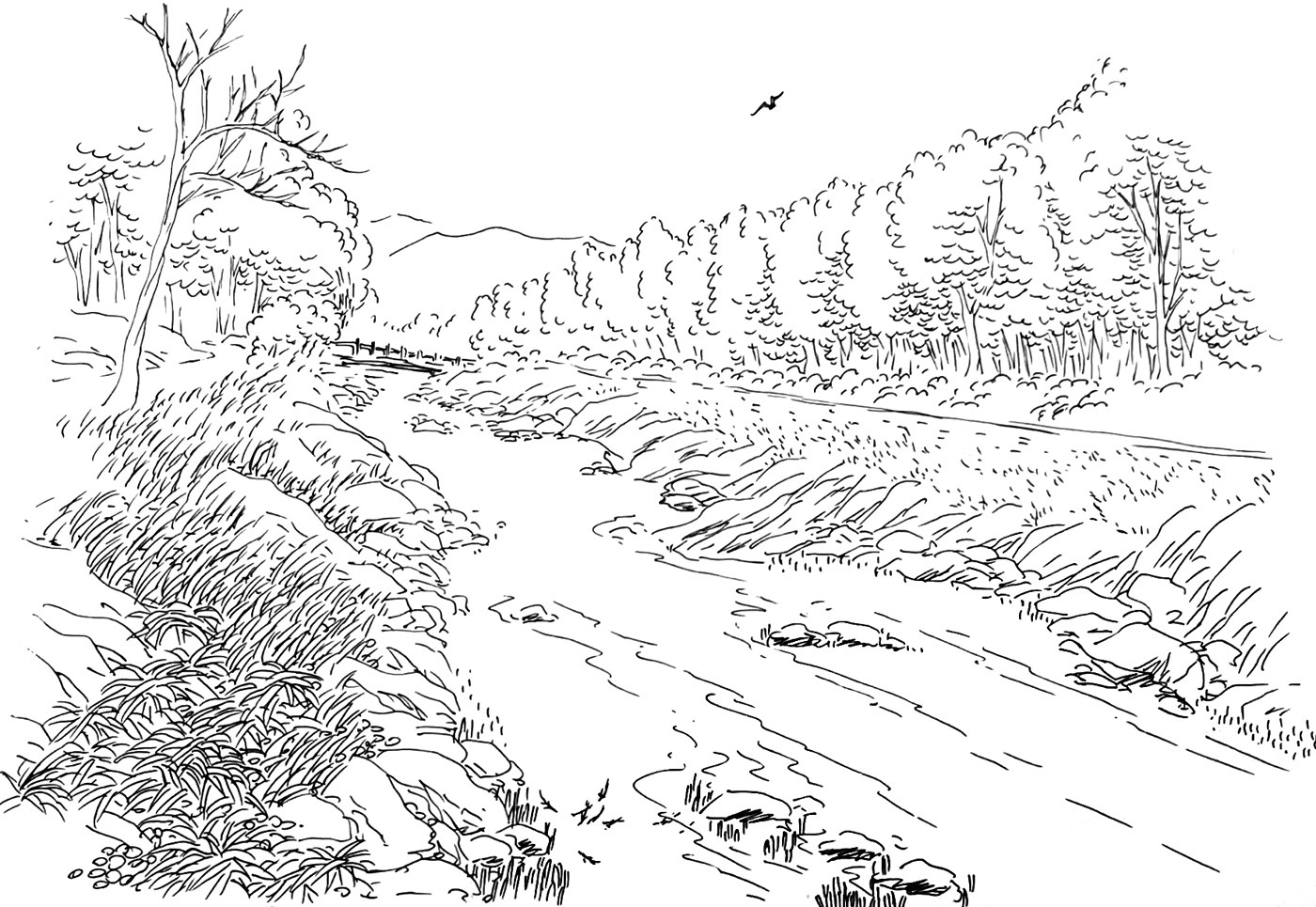
散文空间 | 娘 家
散文空间 | 娘 家
-
散文空间 | 膏壤之上
散文空间 | 膏壤之上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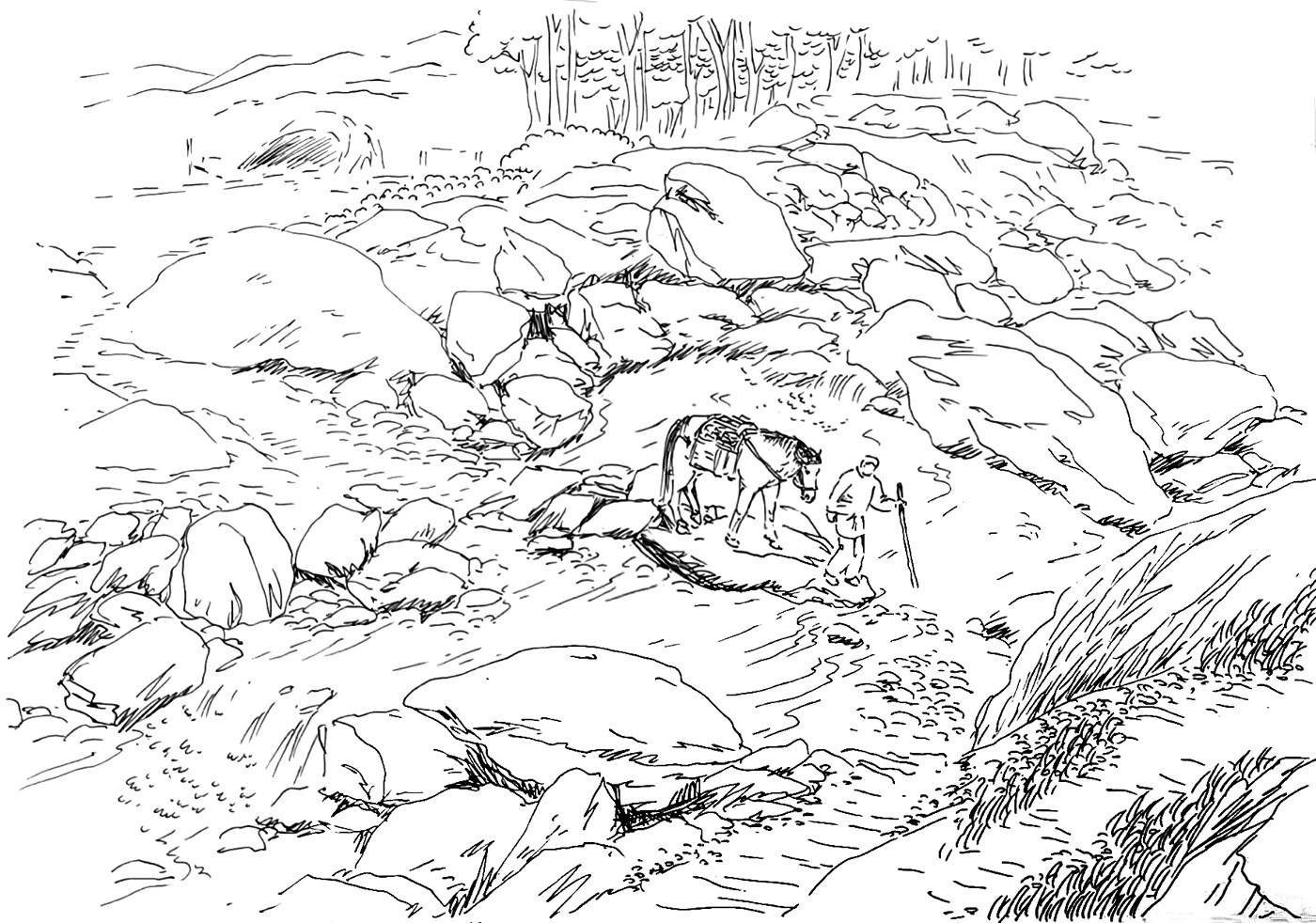
散文空间 | 老屋情长
散文空间 | 老屋情长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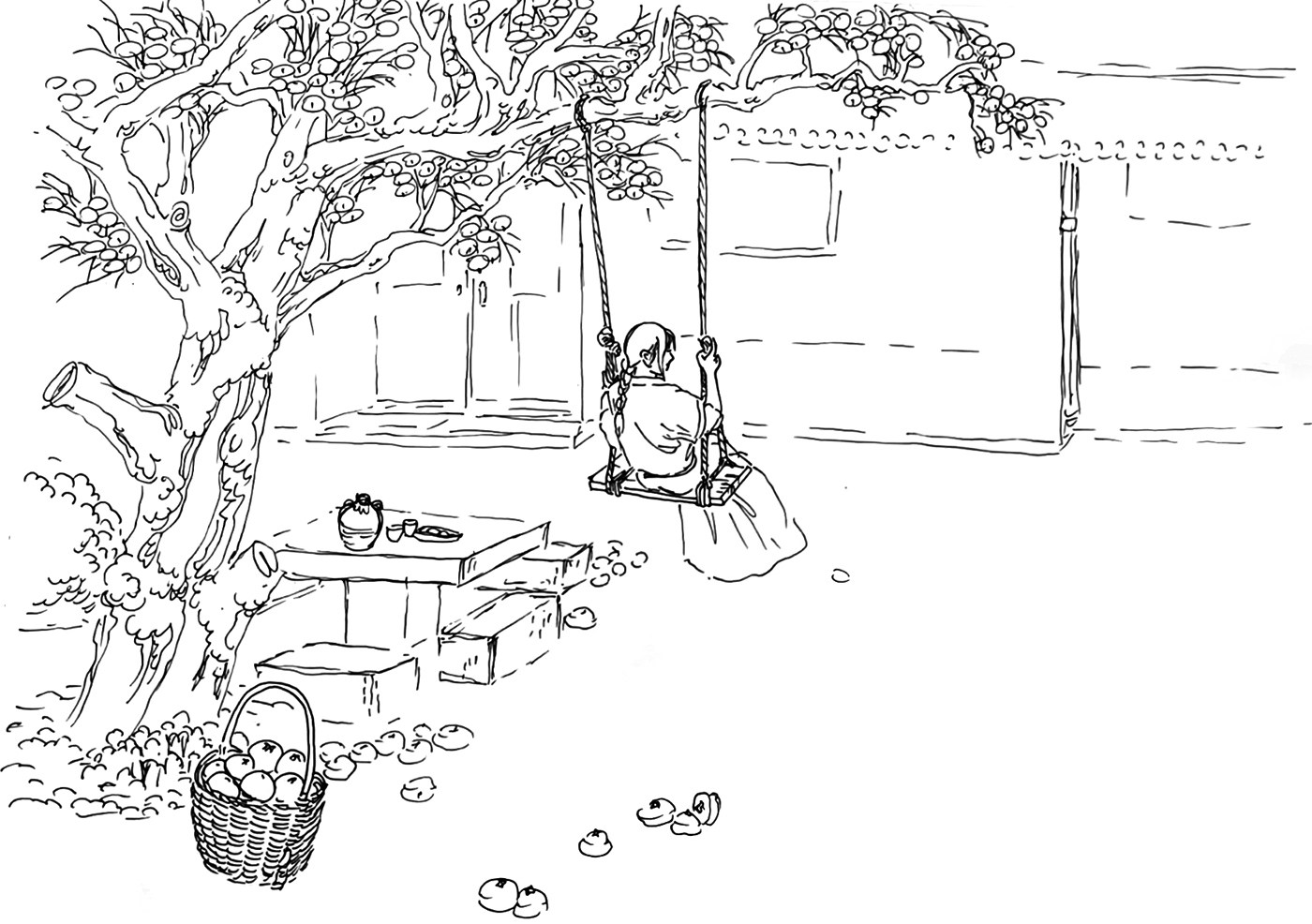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白鹭(外八首)
诗歌广场 | 白鹭(外八首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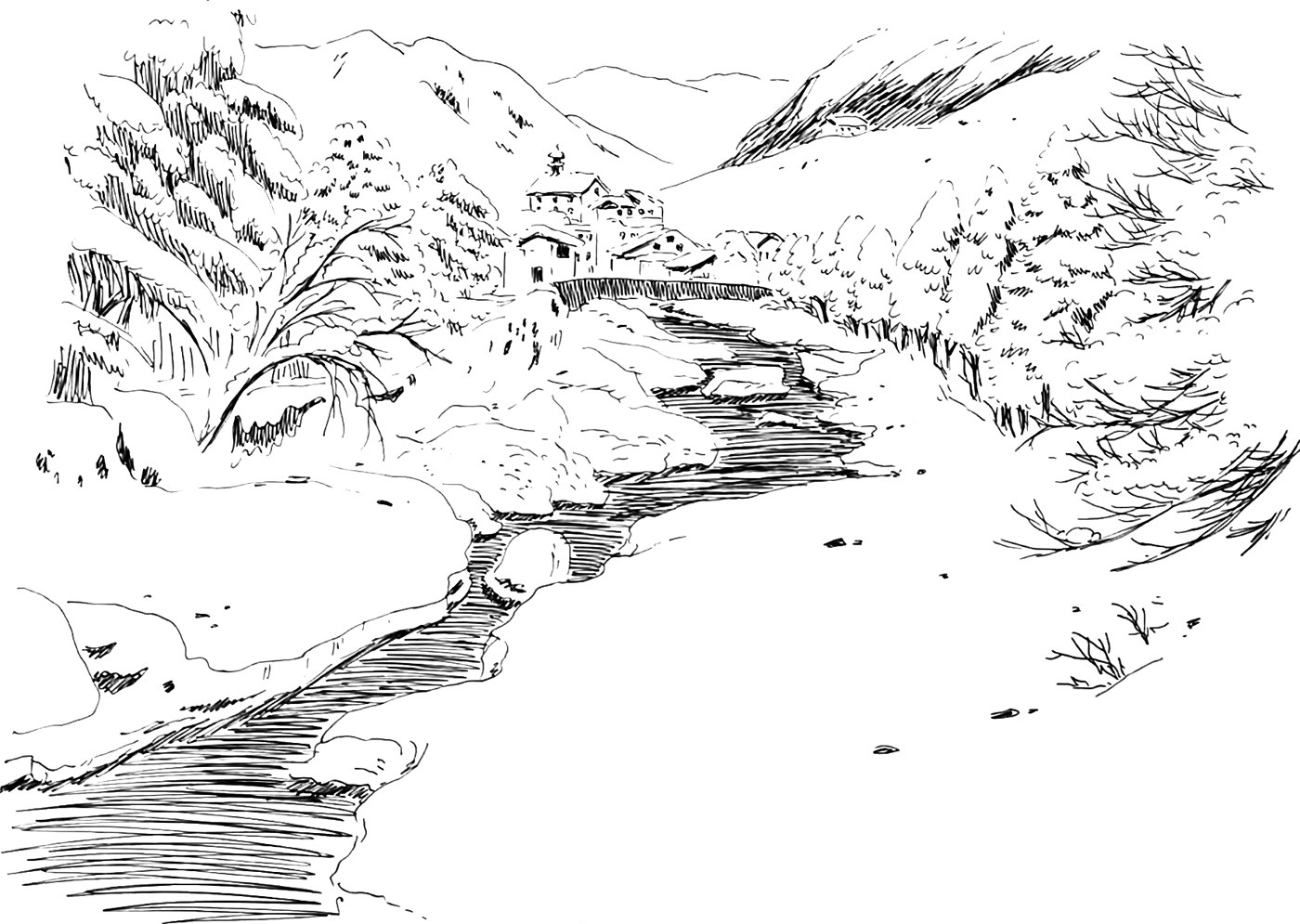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生活之甜(组诗)
诗歌广场 | 生活之甜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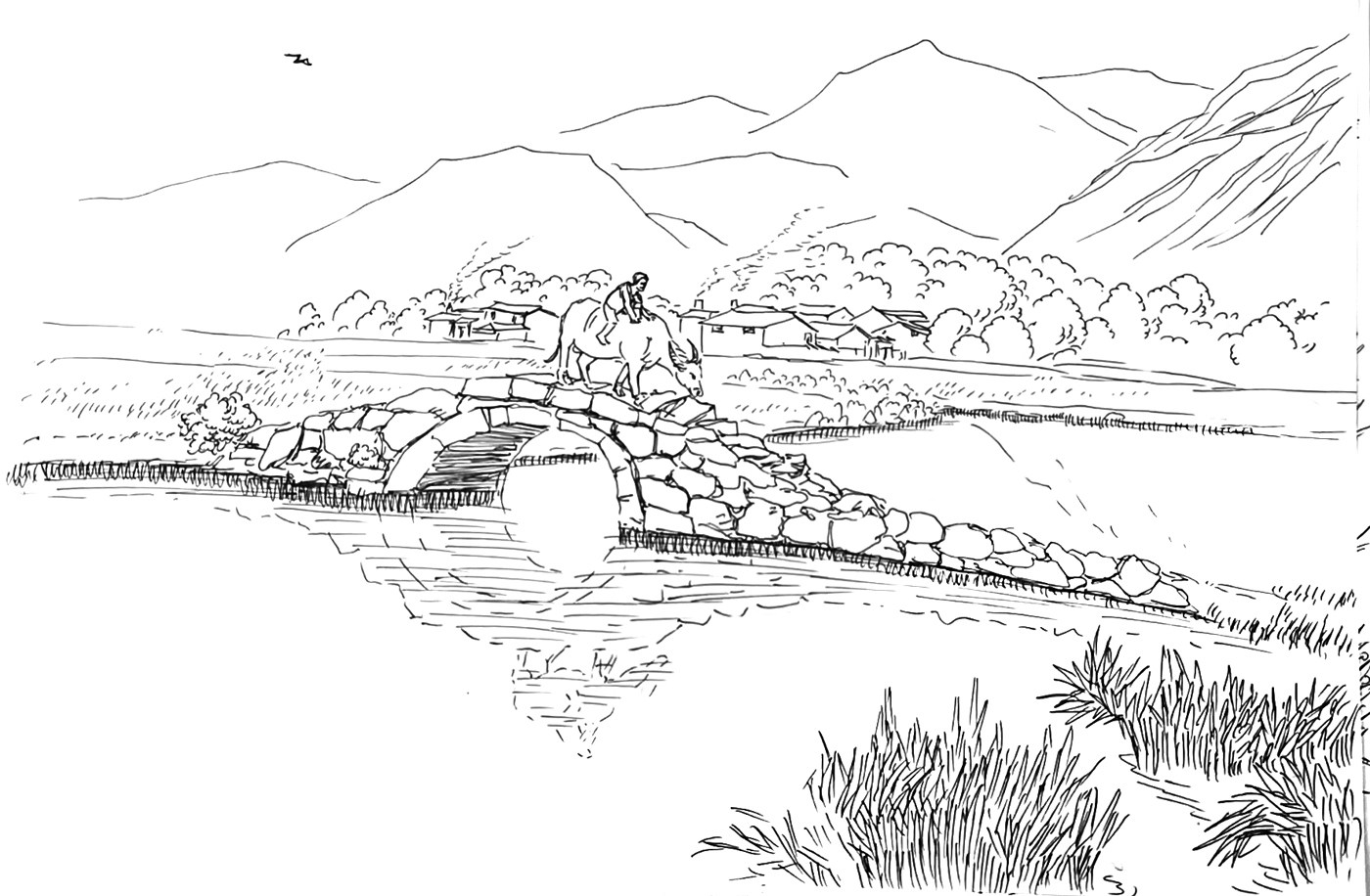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过大理(组诗)
诗歌广场 | 过大理(组诗)
-

诗歌广场 | 皮球(外五首)
诗歌广场 | 皮球(外五首)
-

诗歌广场 | 鸿雁老店(外三首)
诗歌广场 | 鸿雁老店(外三首)
-

诗歌广场 | 苍洱诗萃
诗歌广场 | 苍洱诗萃
-
文艺评论 | 全媒体时代民族地区文化期刊的探索
文艺评论 | 全媒体时代民族地区文化期刊的探索
-

大理旅游 | 漫步阿尼么
大理旅游 | 漫步阿尼么
-

大理旅游 | 南涧行
大理旅游 | 南涧行
-

大理旅游 | 走进东山闭家大村
大理旅游 | 走进东山闭家大村
-
大理记忆 | 渐行渐远的火塘
大理记忆 | 渐行渐远的火塘
-
大理讲坛 | 大唐天空下的漾濞风云
大理讲坛 | 大唐天空下的漾濞风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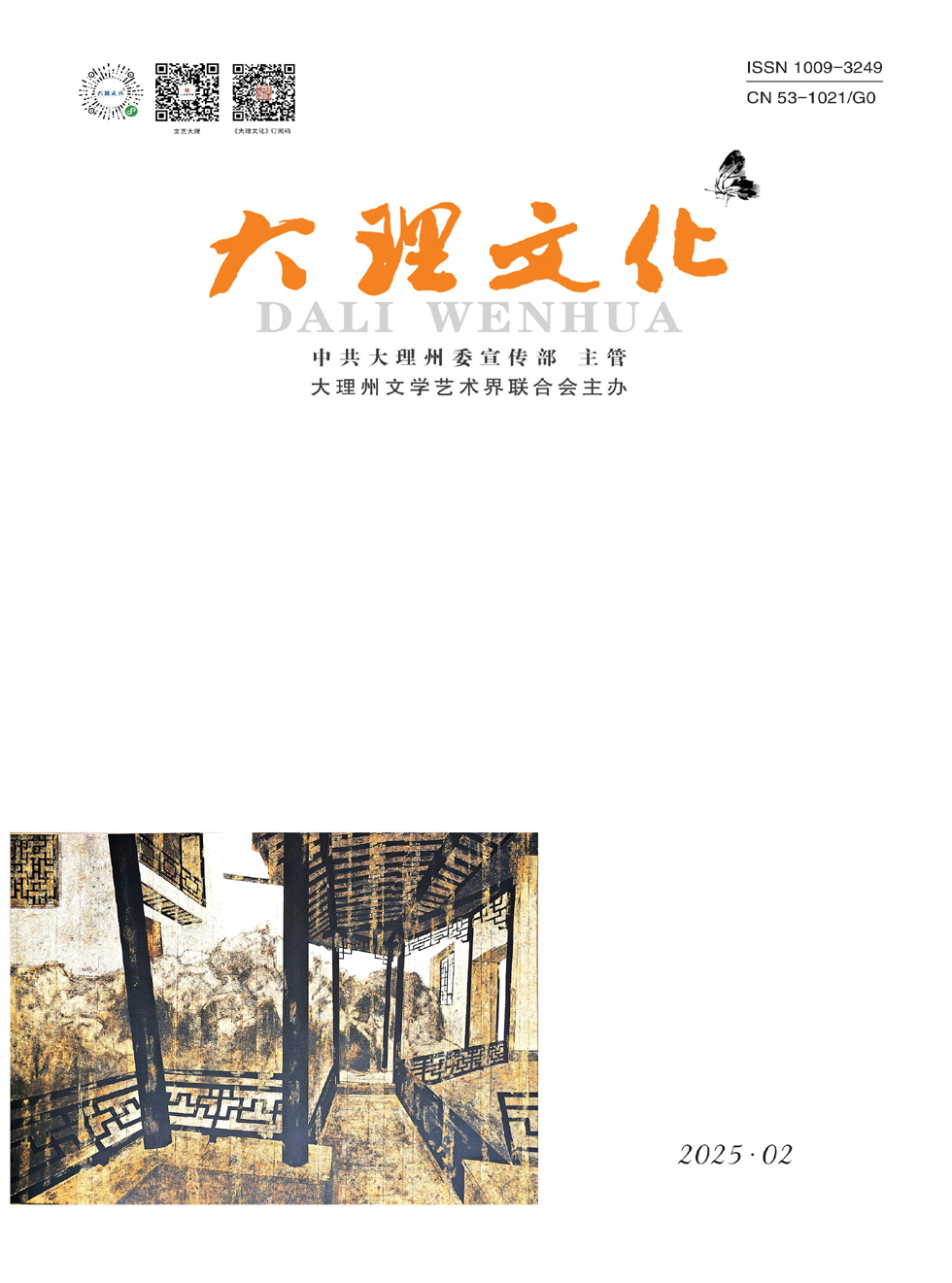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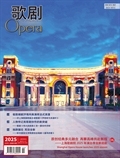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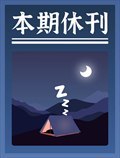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