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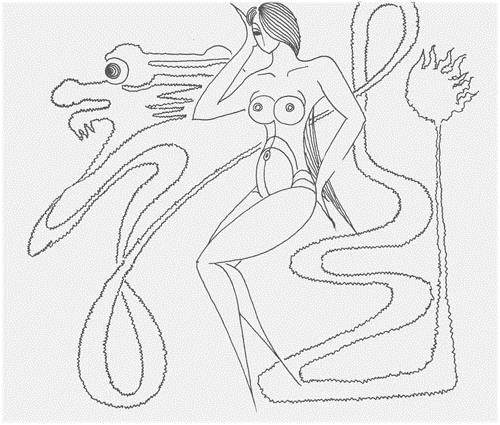
小说 | 一辈子的春天(长篇连载)
小说 | 一辈子的春天(长篇连载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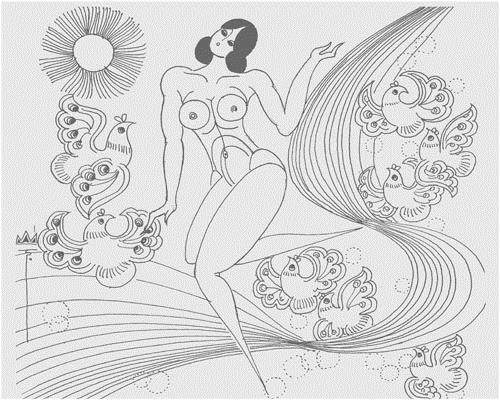
小说 | 江上
小说 | 江上
-
小说 | 哭泣的阿尼玛卿
小说 | 哭泣的阿尼玛卿
-
小说 | 黑痣
小说 | 黑痣
-
散文 | 茉莉为远客
散文 | 茉莉为远客
-

散文 | 望帝耕心
散文 | 望帝耕心
-
散文 | 稻
散文 | 稻
-

散文 | 嘉绒地区的那些鸟儿们
散文 | 嘉绒地区的那些鸟儿们
-
散文 | 河水之虞(外一章)
散文 | 河水之虞(外一章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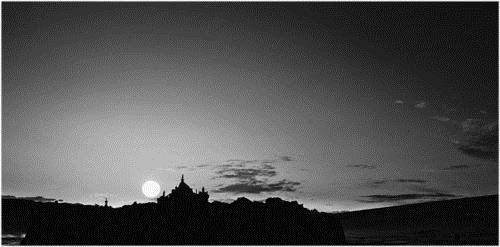
散文 | 行吟亚丁
散文 | 行吟亚丁
-
散文 | 故乡,童年
散文 | 故乡,童年
-
散文 | 梨园春色的悠悠古韵
散文 | 梨园春色的悠悠古韵
-

散文 | 康定的“周末候鸟”们
散文 | 康定的“周末候鸟”们
-
诗歌 | 至简生活(组诗)
诗歌 | 至简生活(组诗)
-
诗歌 | 夜合花(五首)
诗歌 | 夜合花(五首)
-
诗歌 | 缓慢地自燃(组诗)
诗歌 | 缓慢地自燃(组诗)
-
诗歌 | 窗的心事(组诗)
诗歌 | 窗的心事(组诗)
-
诗歌 | 我不想辜负故乡(组诗)
诗歌 | 我不想辜负故乡(组诗)
-
诗歌 | 日松贡布,今生走不尽的旅途(组诗)
诗歌 | 日松贡布,今生走不尽的旅途(组诗)
-
诗歌 | 暮春(四首)
诗歌 | 暮春(四首)
-
诗歌 | 冬天的骨头(外二首)
诗歌 | 冬天的骨头(外二首)
-
诗歌 | 满世界细雨在生长(外一首)
诗歌 | 满世界细雨在生长(外一首)
-
诗歌 | 看不见的波动(外二首)
诗歌 | 看不见的波动(外二首)
-
诗歌 | 三星堆之梦
诗歌 | 三星堆之梦
-
诗歌 | 翻越折多山(外二首)
诗歌 | 翻越折多山(外二首)
-
诗歌 | 冬日来信(外一首)
诗歌 | 冬日来信(外一首)
-
诗歌 | 回家
诗歌 | 回家
-
诗歌 | 有雨的黄昏(外一首)
诗歌 | 有雨的黄昏(外一首)
-
诗歌 | 《贡嘎山》杂志2023年度优秀作品暨授奖词
诗歌 | 《贡嘎山》杂志2023年度优秀作品暨授奖词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